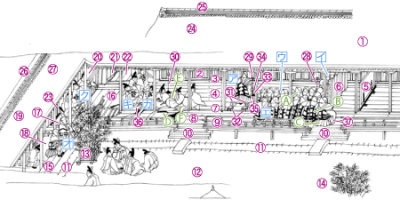为何要研究角色形象呢? 研究角色形象,有何必要性和益处呢? 对这个问题,在上一节叙述了关系到日语教育方面的答案。本节将接续上节,作为第二个答案从语言研究的角度来叙述研究话语角色的意义。说到“意义”,也许读者会想起,像“ウソだよぴょーん(Uso-da-yo-pyôn,说谎的啦pyôn)”中的“ぴょーん(pyôn)”这类,角色助词的“发现”吧。也就是说,原以为句子是以终助词来结束的,但事实上却不是那样的。谁料在终助词[“よ” (yo)]的后面还会出现与说话者的角色形象直接关联的角色助词(“ぴょーん(pyôn)”)。以往的词类的分类中没有去设想角色助词,以往的句子结构观也没有设想角色助词的出现位置。与轻薄的表面印象相反,其实角色助词可以触发词类分类和句子构造观吧。想必这些是很容易理解的内容吧,不过我在这儿那儿写了关于角色助词(详见第1节、第10节、第20节),所以在此就来叙述一下别的意义吧。首先,就来看一下关于省略“ら (ra)”的言辞(“ら抜きことば,Ra-nuki kotoba”)的以下文章吧。
在此来考虑一下省略“ら”的言辞吧。在表达“能看”的意思时,不说“見られる(mirareru)”而说“見れる(mireru)”的是省略“ら”的言辞。以“能睡”的意思不说“寝られる(nerareru)”而说“寝れる(nereru)”的也是省略“ら”的言辞。为什么现在以年轻人为中心,省略“ら”的言辞在蔓延呢?
对此有这样的说明。那是因为在以往的日语语法系统中,助动词“られる(rareru)”的功能太多了。“親に叱られる(Oya-ni shikarareru,被父母骂)”的“られる”表示被动、“お客様が帰られる(Okyakusama-ga kaerareru,客人要回了)”的“られる”表示尊敬。“行く末が案じられる(Yukusue-ga anjirareru,前途令人担心)”的“られる”表示自发、“どうにか見られる(Dônika mirareru, 勉强能看)”的“られる”表示可能。被动、尊敬、自发、可能,助动词“られる(rareru)”要负担4种功能,太不容易了。因此,新一代就把其中的一个“可能”给删除了,将“られる(rareru)”的功能负担从4个减轻为3 个。
这个说明好像很有道理。但是,“られる(rareru)”的功能负担的“不容易”之处,真的是我们的“问题”吗? 我们真的是常常在为“每次说‘られる’的时候,生怕会被误解成其他的意思”或“让对方苦想现在说的这个‘られる’究竟是哪一个‘られる’呢的行为实在是太过意不去了”等等而苦恼吗? 如果说,是为了拯救日语沟通的未来,年轻人们才下定决心使用省略“ら”的言辞的话,那么大人们为何不去称赞省略“ら”的言辞,而是不明事理地痛骂为“没有教养的年轻人使用的不规范的语言”呢? 为何年轻人们不表明自己了不起的动机,还嘀咕着在拜访公司时要注意不去使用省略“ら”的言辞呢?
不光是省略“ら”的言辞,在语法的说明上所提到的“说话者”像,难道不是总是异常地聪明,还被推到理智的位置上吗?
[定延利之《煩悩の文法(Bon’no-no bunpô, 烦恼的文法)》“前言”pp. 10-11, 筑摩书房, 2008.]
事到如今,没想到会从自己的书里使用这么长的引用。无论如何,书中一语道破地写着我的想法(理所当然啊),很方便嘛,还请多多谅解。语言研究者喜欢拿出脱离实际的、异常理智的“说话者”之像这一点,不仅仅是在像省略“ら”的言辞之蔓延这类解释语言变化 (change) 的时候,在解释像行话(使用在特定的职业或集团内部的专门用语、同伴语言、隐语)或年轻人的言辞之类的语言变异 (variety) 的时候也是一样的。
经常会有人从目的论的角度来说明行话,例如,说行话在“为了不被外人察觉意思”、“提高面向集团的归属意识”、“坚固内部者之间的团结”、“若无其事地夸夸其谈自己对业界的内部事情很清楚”、“纯粹地享乐语言的游戏”、“迅速地交换情报”等等的时候很有效果,所以才会创作和使用行话。
的确,特意地创作和使用,这样的解释或许对一些明显的行话时很适合的。但是,也有像“平常是在无意地使用,不过仔细想一想,这个说法在别的集团中会有多大的通用程度呢”这样的难以被发觉的行话。
(25) 我在某机动车的厂子里做点火时期和燃料的设置,整天跟“ノッキング(nokkingu, 爆击)”格斗。在我们公司,“ノッキング(nokkingu)”=高负荷时产生的异常燃烧、是引擎单体上的现象。像オーリィー(Ôrî)说的现象我们说成“サージ(sâji)”或“スナッチ(sunacchi)”,与引擎的“ノッキング(nokkingu)”分开来考虑。(也许是我们公司的方言吧。)(//www.geocities.co.jp/MotorCity/9055/0403egeobook.html, 2005年4月15日) 发布在某电子揭示板 (BBS) 上的短文(25)的笔者写到,自己使用的“ノッキング(nokkingu)”的定义或许只通用于自己的公司,跟对方的不一样。假设即使这个忧虑真是那样的,也没有必要无理地将这个“ノッキング (nokkingu)”与上述的目的意识连接在一起吧。
[中川(モクタリ,Mokhtari)明子・定延利之<専門のことば・仲間のことば(Senmon-no kotoba, nakama-no kotoba,专门的语言、同伴的语言,上野智子・定延利之・佐藤和之・野田春美(编)《日本語のバラエティ(Nihongo-no baraetii,日语的变化)》p. 23, おうふう(OHFU), 2005.]
哎呀,又引用啦。自己写的书就是方便,没辙啊。就是说,也许真的有“为了不让外人察觉”或“为了只跟自己人一起分享快乐”而故意地说行话或年轻人的言辞的时候,但是不也有像在上面所叙述的不是那样的时候吗? 自己本来是没什么目的或意图地说话,但那些话语恰恰就是行话或年轻人的言辞。那个时候,如果像个万事通似的低声私语地挤着眼表示“咱们是为了保守秘密及内部团结吧”的话,也只会一味地羞愧吧。
我们说话时,并不是说“设定某个目的,为了达成目的而有意地使用语言”的行为总是在成立。但是,现在的语言研究中有很多时候是,忘记了本来的“说话者”像,用那样的“上空飞行的思考”(啊呀呀,说出来了)来解决问题。
说起语言的变异,除了像行话或年轻人的言辞的社会性变异,不可忘记的还有个人内部的变异。
一个人能说出来的语言的多样性,远远超出了我们的想象(见第95节)。这个多样性在往常都是被整理到,“说话者根据场合或状况、说话内容或对方而选择最合适的形式,并且根据这个形式而区分地使用语言”的看似很有道理的模型当中。这个整理方式在“选择形式”或“区分地使用语言”这一点上,是以为了达成目的而有意图地使用语言的理智的“说话者”像为前提的,对此并不需要什么说明吧。那么,真的可以把语言的个人内部变异,那样地整理完吗? 也就是说,目的论性的说话观、道具性的语言观,还有可以根据意图运用自如地使用形式的理智的“说话者”像的极限在哪里呢?为了补充其不足的新“说话者”像是什么样的呢?
与可以自在地改变“形式”不同,还有被期待为不变的东西。一旦目睹了变化的过程,虽然马上能察觉到究竟是怎么一回事,(除了开玩笑的文脉)但是看到的人和被看到的人都会感到很尴尬的东西。即,被定为我们不能自由地灵活运用的东西。在这个连载中就是先让大家用“直觉想象到”(见第94节)有这样的东西的确存在于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,并且把它称为“角色形象”,以那样的观点来观察日语社会。(看来日语(现代日语的普通话)这个家伙,与角色形象的关系特别地强烈。正因此,对日语学习者来说会越发地成为问题吧。)
归根结底,在这个连载中所尝试的是,对在上面所举的问题的一个答案,尽量地拿出具体并易懂的形式。当然,这个尝试的成败只能交给读者们来判断了。但是有一点非常清楚的是,通过研究怎样去说明“一个说话者所说的语言是多样的”这一现象,我们一起重新研讨了语言研究的框架(说话观及语言观),并且分享了跃进的机会。将这个说成为在语言研究上研究角色形象的意义,大家没有异论吧。(待续)